朱自清散文《家》全文解析(附:读后感)
我曾经读过冰心老人在80岁时写的一篇散文——《家》。冰心在文章中写到她一生到过很多地方,也住过很多地方,但让她魂牵梦绕的还是她家的老宅,冰心在文章中说,梦里坐洋车回到剪子巷,住着她的父母和弟弟的剪子巷,才是她灵魂深处永久的家。
冰心说:“梦最能暴露和揭发一个人的灵魂深处,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向往和眷恋……”。
家,也许是我们所有人梦里最多去、最眷恋、最牵挂的地方。月是故乡明,家,是诗人心灵最好的最后的归宿。

读着冰心老人80高龄的文字,我仿佛看到了一个耋耄老人在夕阳下,独立桥头,远眺前方,目光灼灼,老泪盈眶,那是她家的方向。
猛然想起两句诗:“日暮乡关何处是,烟波江上使人愁”,是崔颢黄鹤楼中的句子。望着那烟波浩渺的滔滔江水,让人愁的是太阳落山了,家乡啊,你在何方?诗中的“日暮”,难道不可以做“人生之垂暮”之解吗?人在垂垂暮年,往往比年少时更思念家乡,所以自古就有“叶落归根”之说,特别是那些远在异国他乡的人们,即使是生死他乡,也要把尸骨埋在家乡的土地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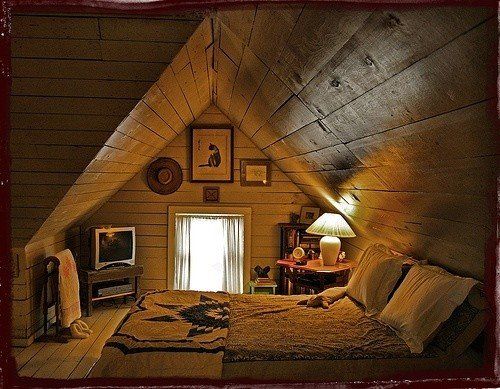
由此看来,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,就是一个由家出发再归来回到家这么一个圆周运动,是一个由一个家到另一个家的漫漫旅程。所以我们说的“在路上”,实际是在回家的路上,是在寻找精神家园的路上。于是便了李白的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,家,是诗人眼中那轮明月;便有了王维的“来日倚窗前,寒梅著花未”中的那朵寒梅;便有了马致远笔下的“夕阳西下,断肠人,在天涯”的九曲回肠;便有了李商隐的“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”的那份期待;便有了王安石的“春风又绿江南岸,明月何时照我还”的似箭归心;便有了“谁家玉笛暗飞声,散入春风满洛城”那撩人的夜曲。

我想,每一个人大概都有两个生命:一个是肉体的,一个是灵魂的。出生时,我们的肉体栖身于父母的家,慢慢长大后,我们不再满足于那个只供我们肉身栖息的家,我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家。于是,我们与爱人一起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家。可是,此时我们的灵魂并没有安分,它逐渐长大成熟并开始不安的躁动,它开始流浪寻找栖息地,它也需要一个“家”,那个“家”不一定很大,却装得下那颗不安分的灵魂;那个家不一定富丽堂皇,却一定要干净明朗,免得把灵魂弄脏。这个家是一个人灵魂的栖息地,是一个人的全部精神之所在,是一个人魂之牵,梦之绕。有了这个家,我们就可以抵抗任何风雨,不惧怕任何风暴。

可是 ,我的那一个“家”在哪里呢,在普救天下的《圣经》里吗?在爱人的心里吗?在我爱的文学里吗?又想起崔颢的那两句诗,“日暮相关何处是,烟波江上使人愁” 。家,也许,就在你暮然回首时的灯火阑珊处。

